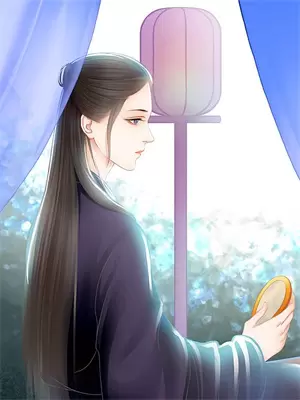我叫季晓,一个瑜伽教练,生活简单得像一条直线。直到我那个离婚两年,
早就老死不相往来的前夫,死在了他自己的公寓里。警察找上门,
因为他手机里最后一条暧昧不清的聊天记录,来自我。一夜之间,我成了头号嫌疑人。
为了自证清白,我搬回了我们曾经住过的老房子,试图找到一些他留下的线索。
但从我住进去的第一晚开始,怪事就没停过。墙壁里传出指甲刮擦的声音,
只在深夜响起的脚步声,还有镜子里一闪而过的不属于我的影子。所有人都说我疯了,
是巨大的压力让我产生了幻觉。连我最好的闺蜜童瑶,都劝我去看心理医生。我去了。
那个叫卫哲的心理咨询师,冷静,理性,用一套套理论分析我的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。
可我知道,那不是幻觉。有些东西,是真的。它在黑暗里看着我,想把我拖进深渊。
而当我终于看清那东西的脸时,我才明白,这世上最恐怖的怪谈,不是鬼,是人心。
11.警车停在瑜伽馆楼下的时候,我的会员们正做到下犬式。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,
铺了一地金黄,空气里都是精油好闻的味道。一切都挺岁月静好的。
直到两个穿制服的男人推开门,打断了我的口令。“季晓?”为首的那个国字脸,
眼神挺利索。我点点头,从垫子上站起来。学员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钉在我身上,好奇,探究。
“我们是市局的,”他亮了一下证件,“有点事想跟你了解一下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但我还是挺镇定的,对着学员们笑了笑。“大家先自己练习一下核心,我去去就回。
”我跟着他们走到门外。走廊的风有点凉,吹得我后背的汗都干了。“什么事?”我问。
国字脸没绕弯子。“陆一鸣死了。”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陆一鸣,我前夫。离婚两年,
除了每个月银行卡上会多一笔他支付的赡养费,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。
像个早就从我生命里删掉的程序,只是每个月还会弹个窗。“死了?”我重复了一遍,
觉得这俩字特别不真实。“初步判断是昨晚死的,煤气中毒。他的邻居闻到味道不对报了警。
”我哦了一声。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说节哀?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说活该?好像也不至于。
“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回局里一趟,配合调查。”我皱了下眉:“我是他前妻,不是现任。
这事跟我有关系吗?”另一个年轻点的警察开了口,语气挺冲。“有没有关系,
不是你说了算。”“我们在他手机里,发现最后一条通讯记录是你的。”“时间,
昨天晚上十一点半。”2.市局的空调开得跟冰窖一样。我坐在审讯室里,
手里的纸杯都快被我捏变形了。对面的国字脸叫李队,负责问话。年轻那个在旁边做笔录,
看我的眼神,就跟看一个已经定了罪的犯人。“说说吧,昨天晚上十一点半,
你给他发了什么?”李队问。“我没有。”我说的实话。我的手机就在桌上。他们可以查。
“那你怎么解释这个?”李队把一个证物袋推过来。里面是陆一鸣的手机,屏幕碎了一角。
屏幕上,是我和他的聊天界面。最后一条消息,确实是我发的。“你再逼我,
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”后面还跟了个刀子的表情。我看着那行字,浑身的血都凉了。
这不是我发的。我昨天晚上十点就睡了。“这不是我发的,”我抬头看着李队,
“我的手机一直在家里充电,我压根就没碰过。”“家里还有谁?”“就我一个。
”年轻警察冷笑一声:“那就是手机自己长手发的消息?”我没理他,看着李队。
“警察同志,我跟他两年前就离婚了,离得挺难看的,财产分割闹了很久。但我犯不着杀他,
他死了,每个月给我打钱的人就没了。我图什么?”这是最实在的杀人动机问题。我没动机。
李队盯着我看了很久,没说话。笔录做完,他们拿走了我的手机做技术鉴定。临走前,
李队跟我说:“最近别出本市,随叫随到。”我走出市局大门,天已经黑了。冷风一吹,
我才发现自己连件外套都没穿,身上还是那件单薄的瑜伽服。我打了个哆嗦,拦了辆出租车。
回家的路上,我脑子一团乱。那条消息到底是谁发的?黑客?
还是说……陆一鸣自己用我的账号发的?为了陷害我?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他都已经死了。
3.我住的地方是个老小区,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半年了,一直没人修。我摸黑爬上五楼,
用钥匙开门。一进屋,没开灯,直接把自己摔在沙发上。太累了。不是身体累,是心累。
跟陆一鸣那段婚姻,几乎耗干了我半条命。他出轨,家暴,堵伯。我提离婚,
他就拿我父母的工作威胁我。折腾了一年多,我身上添了不少伤,才终于把婚离了。
我以为噩梦早就结束了。没想到,他死了,还要再拉我一把。手机被收走了,
我也联系不上别人。我最好的闺蜜童瑶,最近出差了,要去一个星期。我躺在黑暗里,
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,感觉自己像一座孤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听见了一点声音。
不是窗外的风声。是从墙里传来的。“叩,叩叩。”很轻,很有节奏。像是有人在用指甲,
慢慢地敲墙。我一下坐了起来。我们这楼隔音不好,邻居夫妻吵架我都能听见。但这声音,
不是隔壁的。它好像……就在我这间屋子的墙里。“叩,叩叩。”又响了。
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房子是我跟陆一鳴的婚房。离婚后,房子判给了我,他就搬出去了。
我一个人住了两年,从来没听见过这种声音。我壮着胆子,走到发出声音的那面墙边。
是卧室的墙。我把耳朵贴上去。“叩,叩叩。”声音更清晰了。冰冷的墙壁,
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寒意。我猛地退后两步,撞到了身后的椅子。
椅子倒地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特别响。而那个敲墙的声音,也一下子停了。整个世界,
瞬间安静下来。安静得……可怕。我站在客厅中央,心脏跳得跟打鼓一样。我知道,
从今天开始,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21.我一夜没睡。或者说,不敢睡。
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,只要一闭上眼,就能听见那个“叩叩”声。天亮的时候,
我顶着两个黑眼圈,决定去看看隔壁。说不定是邻居家的声音。我得给自己找个合理的解释,
不然我真得疯。隔壁住着一对小夫妻,平时挺爱吵架。我敲了半天门,没人开。
下楼问了单元的楼长阿姨,才知道他们上个星期就出去旅游了,要去半个月。我站在楼下,
看着自家那个黑洞洞的窗户,一股寒气从脚底板升起来。不是邻居。那会是谁?我回到家,
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。墙,地板,天花板,我都敲了一遍。是实心的。不可能藏人。
难道是楼上或者楼下的?可那声音,真真切切地,就像在我耳边响。我没办法,
只能先去上班。瑜伽馆里人多,阳气重,能让我暂时忘了这事。
可学员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估计警察来找我的事,已经传遍了。我假装没看见,
一节课上完,嗓子都快哑了。下课后,我刚想走,被一个相熟的会员王姐拉住了。“季晓,
你没事吧?我听说了,你可别往心里去,我们都相信你。”我扯了扯嘴角:“谢谢王姐。
”“你那前夫,就不是个东西,死了也是活该。你可千万别被他再缠上。”王姐是好心。
可“缠上”这两个字,像根针,一下子扎在我神经上。我勉强笑了笑,找了个借口就走了。
回到家,天还没黑。我做的第一件事,是去买了把新锁,把门反锁了两道。
然后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,放在卧室那面墙的墙角。如果今晚还有声音,我必须录下来。
这是证据。不管是人是鬼,总得有个说法。2.我蜷在沙发上,开着客厅的灯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十点,十一点,十二点。什么都没有。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
我开始怀疑自己,是不是昨天太紧张,出现幻听了?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。“叩,叩叩。
”又来了!跟昨天一模一样的时间,一模一样的节奏。我一个激灵,瞬间清醒。
我死死地盯着卧室的方向,大气都不敢出。录音开着。我告诉自己,别怕,录下来。
声音持续了大概五分钟,然后停了。我等了半个小时,确定没有再响,
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,拿起手机。我点开录音,把音量调到最大。播放。录音里,
只有一片安静的电流声。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清晰的,让我一晚上没睡的敲击声,
根本就没被录进去。怎么会这样?我把录音反复播放了十几遍。真的没有。那一刻,
一种比恐惧更深的绝望,把我整个罩住了。如果连机器都录不到,
那是不是意味着……这声音,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?我疯了?还是说,这东西,
就是冲着我来的?3.第二天,我决定去找个心理医生。童瑶之前跟我提过一个,
说挺有名的,叫卫哲。我必须找个人聊聊。我需要一个权威的人来告诉我,我只是生病了,
不是见鬼了。卫哲的诊所在一栋写字楼里,装修得很简洁,让人感觉很平静。
他本人比我想象的要年轻。穿着干净的白衬衫,戴着金丝眼镜,看起来斯斯文文。
我坐在他对面,有点紧张。“季小姐,”他看了看我的资料,“你说你最近出现了一些幻听?
”我点点头,把前夫死了,我被警察怀疑,还有墙里的声音,都说了一遍。我说得很乱,
但卫zhe一直很耐心地听着,没有打断我。等我说完,他才推了推眼镜。“根据你的描述,
你最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前夫的突然死亡,以及警方的怀疑,
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应激事件。”“在这种情况下,出现一些感知上的错乱,
比如幻听、幻视,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这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,或者说,
是一种功能失调。”“那个敲墙声,很有可能就是你内心焦虑的一种投射。
”他的声音很温和,很有说服力。他说的一切,都合情合理。
但我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在说:不是的。那不是幻听。那声音太真实了。“那我录不到声音,
也是因为这个吗?”我问。“是的。”卫哲点头,“因为声音只存在于你的大脑里,
现实中它并不存在,录音设备自然也无法捕捉。”他给我开了一些安神的药,
建议我做几次心理疏导。我拿着药走出诊所,心里空落落的。我好像应该松一口气,
因为我只是病了。可我为什么,一点都轻松不起来呢?晚上,我吃了药。药效很好,
我很快就睡着了。睡得很沉,一夜无梦。第二天早上,我醒过来,觉得精神好了很多。
也许卫哲说的是对的。我洗漱完,准备去上班。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,我愣住了。
门口的鞋柜上,放着一只鞋。一只男士皮鞋。是陆一鸣的。这双鞋,在他搬走的时候,
早就被我扔掉了。现在,它就这么安安静静地,出现在我的鞋柜上。鞋尖上,
还沾着一点新鲜的,湿漉漉的泥土。31.我盯着那只鞋,至少有三分钟没动。
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不是我的幻觉。这是一只实实在在的皮鞋,我可以伸手碰到的东西。
我昨天回家,把门反锁了两道。我睡觉前,检查了所有的窗户。这只鞋,是怎么进来的?
我第一反应是报警。但手刚碰到口袋,我就停住了。报警怎么说?
说我家里出现了一只我前夫的鞋?警察只会觉得我精神不正常,更加深对我的怀疑。
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戴上手套,小心翼翼地把那只鞋用塑料袋装起来,藏到柜子最顶上。
然后我开始检查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门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。窗户也关得好好的。屋子里,
除了那只鞋,没有任何东西被动过。就好像,它真的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我坐在沙发上,
后背一阵阵发冷。有人进过我的房子。一个我不知道的人。在我睡着的时候。这个人,
知道我跟陆一鸣的关系,知道我最近的处境。他留下这只鞋,是在警告我?还是在恐吓我?
又或者……他才是杀了陆一鸣的凶手,现在想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?我越想越害怕。
就在这时候,门铃响了。我吓得一哆嗦,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。我从猫眼里看出去。
门口站着的人,是童瑶。我最好的闺蜜。2.“你怎么回来了?不是说要一个星期吗?
”我打开门,有点惊喜。童瑶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,拖着个小行李箱。
“那边项目提前搞定了,我就赶紧飞回来了。不放心你。
”她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童瑶的拥抱很暖,让我紧绷了好几天的神经,
终于松懈了一点。“看你这黑眼圈,都快掉地上了。这几天怎么过的?”她一边换鞋,
一边心疼地看我。我把她拉到沙发上,把所有的事情,都跟她说了。从警察找我,
到墙里的声音,再到今天早上那只诡异的皮鞋。童瑶听完,脸都白了。“太过分了!
这肯定是有人在搞你!不行,我们得报警!”“没用的,”我摇摇头,“没有证据,
警察不会管的。”“那怎么办?就这么让他欺负你?”童瑶气得不行。“我不知道。
”我真的很迷茫。童瑶握住我的手:“别怕,我回来了。我陪着你。”“要不,
你这几天搬我那儿去住吧。你一个人住这,我实在不放心。”我想了想,还是拒绝了。
“不行。如果我走了,那个人肯定会更得意。我倒要看看,他到底想干什么。”我不能跑。
跑了,就等于认输了。“你这脾气……”童瑶叹了口气,“行吧。那从今天开始,
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。两个人,总有个照应。”我看着她,眼睛有点热。在这个时候,
还愿意冲到我身边,不离不弃的,也只有她了。3.童瑶的到来,确实让我安心了不少。
她执行力很强,当天下午就拉着我去买了好几个监控摄像头。大门口装一个,客厅装一个,
卧室门口也装一个。她说:“我就不信了,是人是鬼,总得在镜头底下现形。”晚上,
我们俩叫了外卖,窝在沙发上看电影。有她在,那个老房子好像也没那么阴森了。看着看着,
童瑶突然问我:“对了,你去看心理医生了?那个卫哲,怎么样?”“还行吧。挺专业的。
”我说。“他怎么说?”“他说我压力太大,产生了幻听。”童瑶撇了撇嘴:“这些医生,
就知道纸上谈兵。你这明明就是被人给阴了。”我没说话。其实我心里也更倾向于这个解释。
但那个录不到的声音,还是像根刺一样,扎在我心里。“你跟他……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?
”童瑶又问,语气有点小心翼翼。“什么不该说的?”我没明白。
“就是……关于陆一鳴的那些事。你懂的,有些事,不能跟外人说。”我愣了一下。
我跟陆一鸣之间,确实有些事,只有我和童瑶知道。比如他曾经在外面借了高利贷,
是我跟童瑶凑钱帮他还的。比如他曾经动手打我,是童瑶半夜开车来接我,带我去医院的。
这些事,我确实没跟卫哲说。我觉得没必要。“放心吧,我没说。”我拍了拍她的手。
童瑶这才松了口气,笑了笑:“那就好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”那天晚上,
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。我睡得特别踏实。墙里的声音,没有再响。好像因为童瑶的到来,
那个藏在暗处的东西,也暂时退缩了。我当时真的以为,只要童瑶在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我真是太天真了。41.接下来的几天,风平浪静。敲墙声没再出现,
也没有新的诡异事件发生。监控摄像头24小时开着,录下的都是我和童瑶的日常生活。
警察那边也没再找我。我甚至开始觉得,之前的一切,可能真的只是个恶作剧。
那个留下皮鞋的人,看到我有了防备,就收手了。童瑶看我精神好点了,也开始正常去上班。
只是她每天下班都准时回来,晚上也坚持陪我一起睡。“在你这事彻底解决之前,
我就是你的贴身保镖。”她开玩笑说。我挺感动的。这天晚上,童瑶公司临时有事,要加班。
她给我打了电话,让我自己先吃饭,别等她。挂了电话,屋子里一下子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那种熟悉的,不舒服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我随便吃了点东西,就早早上床了。我不敢关灯。
开着卧室的灯,抱着被子,强迫自己睡觉。半夜,我被渴醒了。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,
想去客厅倒杯水。卧室的门虚掩着,客厅的监控摄像头,正对着我这个方向。
那个红色的小灯,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。我揉着眼睛,走出门。
就在我跟客厅的监控摄像头擦身而过的时候,我眼角的余光,好像瞥到了什么东西。
我猛地回头。监控摄像头的镜头,像一只冰冷的眼睛,正对着我。镜头旁边,墙上,
有一个影子。一个人的轮廓。很高,很瘦。不是我的。我的影子,就在我脚下。那个影子,
像是从墙里透出来的。一动不动,就那么立在那里。我当时脑子就炸了。浑身的血液,
一瞬间冲到头顶,又在一瞬间冻结成冰。我僵在原地,一动都不敢动。
我死死地盯着那个影子。它也“看”着我。我们俩就这么对峙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
那个影子……动了。它非常缓慢地,抬起了一只手。像是在跟我打招呼。我再也忍不住了,
尖叫着冲回卧室,“砰”地一声摔上门,反锁。我背靠着门,浑身抖得像筛糠。我完了。
这不是幻觉。监控摄像头……它肯定也拍到了!2.我一夜没敢出卧室的门。直到天亮,
听见外面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,是童瑶回来了。“晓晓?你怎么了?”她一进来,
就看到我脸色惨白地坐在地上。
我抖着手指着客厅:“监控……快看监控……”童瑶立刻打开手机APP,调取昨晚的录像。
她把进度条拉到我说的那个时间点。我们俩,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。画面上,
我迷迷糊糊地从卧室走出来。然后我停住了,猛地回头,看着摄像头的方向。紧接着,
我就像见了鬼一样,尖叫着跑回了卧室。从头到尾,画面里,只有我一个人。墙上,
干干净净。什么影子都没有。“怎么会……”我喃喃自语,
“我明明看见了……它还对我招手了……”童瑶抱住我,轻轻拍着我的背。“晓晓,
你别吓我。你看,真的什么都没有。”“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,眼花了?”我抢过她的手机,
把那段录像反复看了十几遍。真的没有。又是这样。跟那个录不到的声音一样。
所有诡异的东西,都只为我一个人“上演”。“我没疯!”我冲着童瑶喊,眼泪都下来了,
“我真的看见了!它就在那儿!”“好好好,你没疯,我相信你。”童瑶抱着我,
像在哄一个小孩。可她的眼神里,充满了担忧和……一丝我看不懂的怜悯。我知道,
她也不信我了。她也觉得,我病了。病得很重。3.我觉得我快要被逼疯了。
我给卫哲打了电话,预约了下一次的咨询。我必须找个人证明我没疯。
我带着那段监控录像去了卫哲的诊所。他看完视频,表情没什么变化。“季小姐,
我理解你的恐惧。但在视频里,确实没有你说的那个影子。”“那我看到的是什么?
”我追问。“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,叫‘恐怖谷效应’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与人相似,
但又不是人的东西时,会产生强烈的恐惧和排斥感。”“你看到的那个影子,
很有可能是光影和家具的轮廓,在你的恐惧情绪下,被你的大脑‘补全’成了一个人形。
”又是理论。又是分析。我真的听够了。“卫医生,”我打断他,“你不用跟我说这些。
我就问你,你信不信我?”卫哲沉默了。他看着我,镜片后的眼睛里,情绪很复杂。
过了很久,他才开口。“我信不信不重要。”“重要的是,你得想办法,
让自己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。”“否则,警方那边,会对你非常不利。”他说的没错。
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嫌疑人,在警察眼里,跟一个罪犯也差不多了。我走出诊所,
心里一片冰凉。全世界,好像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。他们都觉得我疯了。
也许……我真的疯了?我站在马路边,看着车来车往。一个念头,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。
如果,那个影子真的存在呢?如果,它聪明到,能避开摄像头呢?或者说,
它能……篡改摄像头的录像?这个念头,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但它像一颗种子,在我心里,
疯狂地生根发芽。我决定,自己查。我不能再指望任何人了。51.我开始像个侦探一样,
分析我身处的这个困局。首先,可以确定的是,有人想害我。这个人,杀了陆一鳴,
并且在想方设法地,把一切都嫁祸给我。他不仅要让我坐牢,还要让我在坐牢之前,
先变成一个疯子。这手段,太狠了。其次,这个人对我非常了解。他知道我住在哪,
知道我的作息,知道我害怕什么。那个敲墙声,那个影子,都是精准地踩在我的恐惧点上。
他甚至能在我装了监控之后,完美地避开镜头,继续作案。这说明,他可能……就在我身边。
或者,他能随时监控我的一举一动。我把家里的监控摄像头,仔細檢查了一遍。
都是我跟童瑶一起买的,最普通的家用摄像头。应该没有被改装过。那问题出在哪?
我开始怀疑卫哲。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,他太容易接近我的内心,也太容易引导我的思维。
他说我产生了幻觉。会不会,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暗示?他在给我催眠?
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我决定再去见他一次。这一次,我不是去寻求帮助的。
我是去试探他的。2.我没有预约,直接去了卫哲的诊所。前台的护士说他正在接待病人,
让我等一下。我坐在休息区,假装玩手机,实际上,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。
大概过了半个小时,卫哲送一个病人出来。他看到我,有点惊讶。“季小姐?你怎么来了?
”“我有点事,想再咨询一下。”我说。他把我带进办公室。还是那个让人平静的房间。
但我现在看这里的一切,都觉得有点不对劲。“坐吧。”他给我倒了杯水。我没喝。
“卫医生,”我开门见山,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“你说。”“如果一个人,
能精准地预判另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,甚至能制造一些‘灵异事件’来摧毁她的精神。
从心理学的角度,这个人,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。卫哲愣了一下。
他推了推眼镜,镜片反射着灯光,我看不清他的眼神。“你说的这种情况,在心理学上,
被称为‘煤气灯效应’,也就是精神操控。”“实施这种操控的人,
通常具有高度的自恋、同理心缺失、以及强烈的控制欲。
”“他们享受将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感觉。”他说得很专业,滴水不漏。
我找不到任何破绽。“那这种人,会是你吗?”我直接把话挑明了。卫哲的表情,
第一次出现了变化。不是惊讶,也不是愤怒。而是一种……无奈。他叹了口气,靠在椅背上。
“季小姐,我知道你现在很警惕,怀疑身边所有的人。这很正常。”“但你有没有想过,
那个真正操控你的人,也许正是利用了你的这种警惕?”“他让你怀疑一切,
让你变得孤立无援。这本身,就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”他的话,像一盆冷水,
从我头顶浇下来。他说得对。我现在就像一只惊弓之鸟,看谁都像是猎人。这样下去,
我迟早会自己把自己逼疯。“那我该怎么办?”我的声音有点抖。卫哲看着我,眼神很认真。
“你需要一个盟友。”“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,并且能帮你从外界客观分析问题的人。
”“这个人,不能是你自己,也不能是你那位……关系过近的朋友。”他说的是童瑶。
我心里一紧。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你们的关系,决定了她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。
她的关心和担忧,有时候,反而会影响你的判断。”“你需要一个局外人。”卫哲站起来,
走到我面前。“如果你愿意,我……可以试试做这个局外人。”我看着他。
阳光从他身后的百叶窗透进来,在他身上打下一道道光斑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眼神很真诚。
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。但就像他说的,我现在,确实需要一个盟友。